喻国明:用“微创新”来适配互联网的“微革命”浪潮|德外荐读
5G技术是一项注定要改变世界、改变传播领域的边界、基点、要素、结构及其机制与规律的革命性技术。本文探讨了5G等新技术所引发的媒介范式的革命,考察了算法作为一种新媒介的特性,进而分析了今天的互联网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强调必须用复杂性范式去认识和把握。 文章以“微版权”的创新为例,强调互联网的“微革命”时代要求我们善于进行一系列的“微创新”。文章提出,解决新技术形式所造成的“信息茧房”效应的关键,不是对某个内容推送的个体提出过分的要求,而是重在完善社会信息供给侧的结构性多元与丰富。文章最后指出,传播学科未来发展的不二法门是建立在跨领域基础上的学科交叉与研究协同。 5G等新技术引发了媒介范式的革命 由于互联网和传播技术的技术革命带来了所谓“百年未遇之大变故”,整个社会和传媒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改变。面对这一系列革命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我们进行学科建设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回到原点,为什么要回到原点?是因为最基础性的东西都发生了改变。 比如说媒介,今天我们最大的困惑就是媒介到底如何去定义。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经说过一句特别具有想象力的话:“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当时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限于对人的物理意义上的延伸,人的听力、人的视觉等等一系列物理性的延伸。 但是今天互联网由于信息技术的革命所带来深刻改变,它开始从一种物理性媒介进入到一种生理性的媒介和心理性的媒介。因为它已经开始实实在在地在万物互联的格局中通过传感器连接我们生理、心理、情绪等各种各样的信号,我们身体与情绪的各种变化起伏,已经通过传感器的数据连接,经由算法跟外界逐渐连为一体。 具体地说,随着5G技术的出现,有越来越多的身体或物件上的感应元件可以实现所谓的万物互联。这种万物互联之后必然会涌现出数量规模及品类极为丰富的全新内容产品——传感器资讯或传感器新闻,它可能要比当年社交媒介把一个个的人连接在一起,赋能于人,使人人都成为传播者,所涌现出来的海量资讯的规模和品类还要大得多,由此给社会和传播领域造成的改变是难以想象的。 而当我们的人体,即我们的生理、我们的心理,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传感器来跟外界进行链接和信息交换的时候,便会由此形成一系列基于全新传播的功能和价值模式,这种巨大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的内外因素的深度链接与“跨界整合”,也带来了对于媒介自身的理解定义的改变,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媒介升级迭代的问题——有很多人觉得这是新闻定义的一种迭代——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革命。 由于数字化技术革命带来的或即将带来的传播边界、传播要素、连接方式、连接场景及其机制规则所发生的一整套改变,连接的对象已经从物理连接达到生理连接和心理连接的复杂系统的境地,这就决定了对于媒介的界定和理解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革命性的改变。 算法即媒介 在强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其实我们实际面对的是弱人工智能。所谓强人工智能就是有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那种人工智能。这样的人工智能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时间范围内还难以出现。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其实都是弱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就是以人为本的,按照人的意志、人的功能、人的能力的一系列延伸。 人工智能是建立在算法基础上的,而算法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媒介,人工智能就是一种算法型的媒介。当然到了强人工智能的时候,或许就不能用媒介来指代。因为它已经独立于我们人之外,成为一种全新主体,我们到时候再用新的范式去认识它。 那么,在弱人工智能作为人体延伸的一种媒介的概念之下,我们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今天我们跟人工智能之间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算法之争、算法推送与编辑推送孰是孰非等,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其实是掌握了现在技术传播生产力的人们,跟过去既有的掌握制度传播生产力的人们之间,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的一种矛盾与对冲,也可以说是一种博弈。 其实是由这两类人的问题产生的,不是人跟人工智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既需要我们传统制度和制度掌握方式的必要改革与调适,也有那些作为新的技术生产力、传播生产力为代表的一方,如何在其野蛮生长中所需要进行的某种磨合修正以及规范化的问题。所以其实两方面都有巨大的调整空间。 新技术引发的传播革命 呼唤制度与规则体系的包容 随着我们的媒介链接的元素和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媒介的结构、边界、规则就要发生改变。在我们既有的游戏规则、既有的制度体系、既有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中,如果不能包容新的因素、新的智慧力量等等,就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社会或者领域的巨大冲撞与消耗。 在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要越来越多地包容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因素。没有这种制度性的包容、规则性的包容,我们的发展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一个制度体系、一个领域的活力,必须有赖于相应的包容,没有这种包容就没有活力,就没有巨大的成长性空间。 对于目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宽容对待。没有这种宽容,就没有技术革命的效应在整个传媒领域的发展与改变。今天的互联网已经远远超出了承载内容的范围,它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架构。由于互联网链接的因素越来越多,就导致了整个互联网领域重心的改变、规则的改变。 互联网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数字化的媒介,由于链接了社会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它一定是一个需要更多包容的现象,在游戏规则方面,把握它的方式就会从过去的那种原子论式的管理方式,进入到生态级的管理方式。所谓生态级的管理方式,就是要求我们用复杂性的观念、复杂性的逻辑、复杂性的范式去管理新传播领域的现象。 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很好:“当你想把所有的错误都拒之门外的时候,真理也只能在门外哭泣。”这就是面对网络这样一个复杂性的生态级意义的社会现象时,我们应该持有的一种重要原则和逻辑。 互联网的“微革命” 要求我们善于进行“微创新” 同样重要的是,在要求我们的制度体系应该包容的同时,也需要我们业内中人根据新的发展形式来进行某种创新性的努力,以实现相应规则的改变。如果我们自己缺少这方面的智慧和努力,我们所面对的游戏规则或治理标准一成不变的话,一定会让我们的发展畏首畏尾,动辄得咎。 所以我们除了要做技术本身的发展之外,还要根据技术逻辑所延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架构、新的态势、新的状态,对游戏规则本身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革与创新。 比如说版权这个概念。这是从互联网诞生以来一直争议的一个话题。版权在传统社会的时候,它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转移利用,但是这不符合互联网建构出来的世界通行规则:互联网构建的是一个“微粒社会”,微资源连接、微价值的利用、微力量的崛起……微革命改变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功能价值形成的转移和利用的状态。所以对于版权,我们认为它也需要做出一些关键性的调整和改变。 一个互联网公司,它要用成千上万的新闻资讯来形成自己的产品,如果说我们都用完整版权的、传统版权的这种方式,去处理相关的收益和转移利用问题,我相信对于互联网内容产业的发展一定是巨大的掣肘,对于由于互联网爆发出来的内容利用的巨大可能性、巨大空间是一种严重的束缚和限制。 所以,能不能建立“微版权”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版权上面我们要允许进行“微分割”,分割到一个个具体的内容表达元素。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对内容(包括视频)的标签标引已经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便利程度。过去如果我们要对一个视频进行标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现在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可以对其中的每一秒钟甚至更小单位的画面元素进行标签化、标引化的处理。这就使我们对整个资源的使用有了一种新的分割利用的可能性。 传统的版权制度下,我对于其中很小的一个片段的使用,必须要买下你整个电影版权、娱乐节目的版权,即整个作品的版权,毫无疑问,这样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比如,我想用一组群星的视频片段来对一位老寿星祝寿,但如果我们可以用“微版权”这个概念来操作,我只用某位艺人在某一个影视作品里边的一个字,他说“祝”,其他人说“老”和“爸”等,一人一个字,一共十个字,请十个明星来祝寿,只花几块钱,就能获得合法的使用版权。这样,就可以激发出社会上有创意能力的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做“微剪族”——其规模和出现的丰富性可能比网红一族来得更加热烈。 版权微化处理后会不会降低版权拥有者的版权收益呢?由于使用者的场域、场景、目的等等极大地丰富和扩大,所以它的版权被盘活之后,版权的收益反而会比整体售卖更加活跃、回报更为丰盈。 有了这个“微版权”之后,未来会兴起一个新的风口级现象,就是微剪辑,就像现在快手、抖音,用自我的表现来形成短视频,而微剪族则能用创意去剪一些小视频,通过剪接的方式表达自我、表达生活、表达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对于传播生产力、对于人类智慧得以释放的一种游戏规则。 一个好的游戏规则对于传播生产力是一种巨大的释放,它会引来新的一轮内容生产的繁荣。所以社交机器人也好、算法型的革命也好,必须要伴随着一系列规则的改变。 任何传播媒介 都存在着某种“信息茧房”效应 我们一提到算法,就认为算法跟信息茧房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提到算法,人们就说怎么来解决信息茧房的问题,好像唯独只有今天的算法才有信息茧房。其实任何一种传播形式、传播的稳定样态,它都有一个稳定的价值结构,这种稳定的价值结构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它的特色,是它独特的功能,但同时也是它的某种局限,如果我们把信息茧房视为局限的话。 任何一种稳定的报道形式之下,都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诉求结构。其实任何一种成熟的传播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一种信息茧房,都有一种改变的必要。比起它自身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信息供给结构的结构性改变。 其实所谓的信息茧房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假设,并且从来没有被研究证实过。解决问题的关键是结构性的改变。如果结构足够多元的话,所谓信息茧房,所谓“灯下黑”的这种局限性就会得到解决。所以不是限制一种算法的问题,而是要发展出更多算法的问题。 今天的算法是通过行为性数据来推测或定义人们的这种需求,如果明天有社交类数据指标进入的话,新的算法对于人们需求的定义一定会有一个巨大改善,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还有各种各样的改善方式,比如说,对于用户在其定义的需求之外随机地投放一定比例的内容,以探测未知领域需求的“冷启动”;再比如,当用户碎片化地抓取和进入信息获取状态时,我们所提供的信息或知识本身是按照知识图谱的方式来提供的,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偏听偏信或“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发生。 传播学科未来发展的不二法门 算法是一种媒介,它不但串联起来人跟物理世界的关联,也把人的生理世界、心理世界联结在一起,来形成更好的社会万物互通的新媒介格局。今天交叉学科的研究汇聚,是当今乃至未来发展传播学科的越来越主流的范式,因为今天传播过程所联结的要素、资源越来越多,它所涉及的领域以及相应的规律机制就越来越多,所以需要多学科之间的共同协同来完成问题的解读与解决。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全才。但在现实生活中确有这样的想法和要求存在。我认为这种要求本身就是对于专业的一种蔑视和不尊重。任何一个专业都是有门槛、有高度的,跨越它都是有相当的难度的。这就是“隔行如隔山”最基本的道理。 有人说“1万小时定律”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来解决问题,终身学习当然不错,但是在传播和传播研究的实践中扑面而来的问题可不是一个两个,可能是十个二十个乃至几十个陌生的概念、陌生的技术,你要用多少万个小时来解决今天不断涌现的种种新问题?今天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等一系列新的技术、新的领域,你能都用1万小时的方式去学习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时间成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成本。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同的学者之间,基于彼此之间的理解,基于彼此之间的互融互通,形成一种协同与整合。这才是今天学科发展及实践进步的不二法门。因为对内容专家来说很难的事情,对技术专家而言很可能易如反掌;反过来说,对技术专家来说很难的事情,比如党和政府对于内容传播的主流化要求,社会的某些适应性法则,有些人工智能专家、技术专家、大数据专家——他们在自己领域里面是大家,但是对于上述这些要求和法则而言,可能比我们专业的一个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了解的还要少。这就是彼此之间互相需要、互相协同的基础。 而今天这样的领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彼此之间的协同与协作。只有这样的协同与整合,我们才能够产生巨大的传播生产力、技术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位教授打车,下了车之后,望着远去的出租车突然急得几乎要崩溃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计算机包忘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上。可他下车时既没打发票,也没有记下出租车的车号,眼看着事情难以挽回,这时候他看到一辆出租车,便迅速把它一把拦下,对着司机着急地说:“师傅,给我追上前面那辆车,我付你一百块钱!”出租汽车司机很沉着地望了前边一眼,说:“你说的是他吗?” “是的是的,请别废话赶紧追啊,要不然就追不上了!”他把一百块钱拍到这司机的手里,说:“快点!”这位司机不急不忙,把一百块钱收好了,然后拿起手机说:“小李小李,请你回来一下,刚才的客人把计算机落在你的后座上了。”你看,对你来说是一个几乎失控的事情,对他来说却易如反掌,尽在掌握之中。跨学科的合作、协同的好处和必要性正在于此。 编者按: 作者: 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CTR媒体融合研究院专家; 来源:新闻界; 内容有删节。













抱团交流
一个集大神卖家与逗趣同行于一体的交流群,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备注“进群”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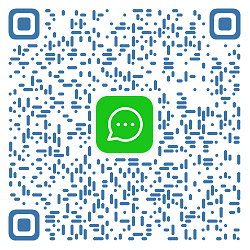
目前100000+人已关注加入我们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AMZ520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